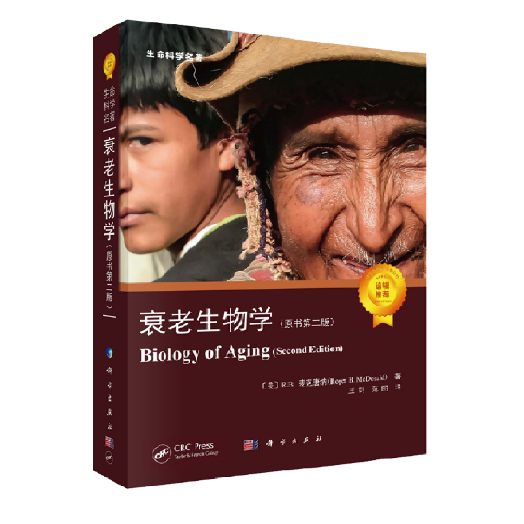张旃不曾想到,17年后,一场考验她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参加过非典救治的她,这一次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冷静且从容。
我做好了被传染的准备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2020年1月18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女医生张旃副教授主动请缨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战斗,写下现代版“与夫书”。
张旃的丈夫是同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工作、担任神经外I科副主任的李明昌教授。同为医者,李明昌有担心,但更多的是对妻子的理解与支持:“我坚决支持她的决定,但我更希望她能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和同事。我等着她凯旋!”
长期在临床参与诊断与救治工作,张旃提交请战书有自己的理由:申请长驻留观室,可免去不停地在院内会诊,既能减轻其他医生负担,病人也可以获得延续性治疗,留观室床位也就流动起来。“如果领导们同意,请告知胡教(注:即科主任胡克),同时停掉我的专家门诊。另外,请加强留观室的防护,固定下谈及请战的心情,她说:“有些事情,想到就去做!敌人来了,上战场就是我的职责。”参加过非典救治的她,这一次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冷静且从容级医生。”张旃交上请战书当天,即获得医院党委的批准。
早在2019年12月中旬,身兼门诊和病房工作的张旃就感觉到了异样:“今年的甲流病人明显增多,且越来越多。”此时的她,被一种“病毒性肺炎”的诊断所笼罩。出于一种职业敏感,她和她的同事们对病人实行了较为谨慎的隔离处理,并在早期便要求患者出院后居家隔离,要求在院病人和家属必须戴口罩。同时要求实习轮科医生不得进病房,强化对医护人员的保护。
12月27日前后,她所在的科室又收治了第二批6名病人,后经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做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特异性Ig G抗体均为阳性,证实他们均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患者。此后,疫情传播的大规模和复杂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每日战斗在病房的张旃随手记录下一线医护人员的高强度工作。
“1月19日,夜班,兼顾发热门诊和二楼留观室。还没到上班时间,就开始接会诊电话。从5时到10时45分,一共24个医疗电话。
“1月20日,8时到17时,54个工作电话,40多个病人查房,全院大会诊3次,急会诊多得不记得了。午间休息10分钟,因为低血糖犯了……”
1月中下旬,媒体陆续爆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出现“人传染人”。风云突变之间,张旃和她的同事们暗暗庆幸,好在一开始就做好了防护措施,所在科室医护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病例!
1月23日,武汉封城。一时之间,整座城市按下暂停键。人们处于极度的惊恐不安之中,甚至包括非呼吸科的医生同行们,也陷入无尽的慌乱之中。“当时没有指导性的文件,也没有太明确的病情防控手册,我们只能按照上级部门和医院的要求层层落实和推进。”在每日确诊和疑似患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张旃的工作变得更为繁忙。医院所处的武昌区霎时成为武汉市疫情最严重的区域,病患最多、确诊最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开始不断提醒身边人不要恐慌:“我们要相信科学,病毒不是完全不可防范,千万不要让慌乱扰乱了我们的心。”
疫情来袭,张旃是医生,更是妻子、母亲、女儿。她仿佛一位勇上战场的女战士,迅速在第一时间做好准备,赶在封城前紧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请父母代为照顾。“我做好了被传染的准备。”张旃笑着说。

上战场就是战士的职责
谈及请战的心情,张旃说:“有些事情,想到就去做!敌人来了,上战场就是我的职责。”“用我力所能及的手段,做好个人防护,同时提醒身边人千万不要恐慌,一定要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就一定能够战胜疫魔。”
张旃认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就是因为公众恐慌,导致大量轻症病人涌入医院造成交叉感染,从而引起疫情进一步扩散。在她看来,呼吸道变异病毒不是第一次侵袭人类,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临床医生今日的临床经验已远胜往昔。
“面对关乎生命的大事,我们会感到焦虑和恐慌——这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但只要仔细想想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来龙去脉以及在临床上治疗患者的资料,就可以得出结论:恐慌完全没有必要。”张旃说。
繁重工作之余,张旃不忘结合临床开展科研思考。“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全新的人类公敌。加深对它的了解并找到对付它的办法,需要我们临床一线医生边治疗边及时总结经验。”点开张旃所在科室的微信公众号,能够查询到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所思所想。
一次查房后,自觉与病人没有接触的张旃换回了外科口罩,但随后她就感觉身体疲乏无力。幸好,经检查她的身体没有大恙。根据自身感受,张旃写下一纸《关注身体给出的信号》,叮嘱一线的医护同行,注意做好自我防护。
“千万千万不要疲劳,这非常重要。”张旃说,“我很怕年轻医生硬扛,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写下‘要注意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在我的认知里,只要感觉到自己不舒服,赶快进行处理,不管是休息也好,或者赶快用药也罢,身体问题就能很快压下去。但如果你忽略它,再一疲劳就很容易发展。这是我非常想跟同行说的话。”
张旃始终认为,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她和她的同事观察到,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首发症状仅为腹泻,怀疑消化系统可能是传播途径。后经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实验室证实,从这些患者的大便和肛拭子中发现病毒核酸。张旃由此再度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建议:临床医师特别是消化内科医师应高度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典型症状,针对患者呕吐物、粪便等做好个人防护。这一重要信息,随后很快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与所有人在媒体上看到的一样,身处一线的张旃每日都要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戴上防护镜进入病区。起初穿防护服耗时耗力,2个多月后,她已经驾轻就熟。有时为了节约防护服,她尽量减少活动轨迹,减少进食。每天,她都要去病房查房,与她的病友们见面,详细询问了解他们的治疗进展,为他们做好心理疏导,聆听病友的心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曾一度同时分管4个病区、100张床位,有一天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晚上8点,中间只用10分钟匆匆吃了一顿饭!
连续60多天,张旃一直战斗在抗疫一线。面对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她顾不得任何喘息,只想尽自己最大努力挽救更多的生命。她性情随和,在与病人生死与共的相处中,早已成了朋友。在她看来,自己必须每天都要出现在房。
“对于病人来说,精神科医生说再多的话,抵不过专科医生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出现,这是一份无言的默契,也是我对他们的期许。”
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不同的病区之间反复巡查,每一次她查房时,病友们隔
着老远都能听到她喘粗气的声音。大家很心疼她,每天早上快查房的时候,就预先准备好一个板凳放在病房的最中间。等她到了,大家就要求她先坐下,再一个个汇报病情。“张教授大部分时间都没坐,有时候看得出来,实在太累了,就先坐下休息一会儿。说休息,其实也就是腿脚休息了一下,脑袋和嘴巴还在跟着我们转呢。”一位康复出院的病友说。
为减少接触,细心的张旃还通过微信解答病患的咨询,为他们减少来回奔波医院的繁琐并在心理上给予大家鼓励和安慰。“张旃教授不仅很敬业,而且我很专业。因为每个人的病情、症状不一样,而国家的新冠治疗方案也没有完全确定,都还在摸索。所以,张教授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症状,在前期治疗的基础上,又采用了不同的治疗方案,为我们积极地想办法。看到她所做的这些,感觉跟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的理念很一致:治疗方案不是写在书本上,而是在每个病人身上。”

希望尽快建立完善的医疗救助体系
2003年,张旃就职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曾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役,承担了大量SA R S患者救治工作。正是在这一次战役汇中,她学会了沉着冷静、科学应对。回忆当年的经历,张旃说:“有一次主任在给一位病人做插管手术时,在场的所有医生开始咳嗽。当时大家并没有在意,后来也没有发病。此后大家才意识到这位病人肯定是非典病人。可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场的人下?”张旃仔细地思考过原因,她认为在于当时的病房通风条件非常好。而这一经验,也沿用到了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
此次抗疫,张旃付出了百分百的投入。2月初,她就自己经诊的一对确诊新冠肺炎夫妻的诊断治疗过程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国病毒学》杂志上,给许多的临床医生和大众提供的及时的救治参考依据。
从1月18日开始,张旃始终在急诊留观室和病房区坚守直面疫情。在门诊,她的工作习惯是热情接待每一位患者,并把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交待得清清楚楚。许多病人总是会慕名前来复诊,有一对老年夫妻更是为了给她送年货专门挂她的专家号,为此,她泪湿眼眶:“每当社会上出现不和谐之声时,我就会想起工作中碰到的这许许多多的让我感动的患者。他们就是我从医生涯坚持的动力......”
万幸的是,此次抗疫中,张旃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样。对此,她理解为“有专业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在救治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并目睹过病人“一床难求”的痛楚,冷静下来,她尤为关注的是思考如何建立完善的医疗救助系统。“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政 府官员,在疾病面前,只有医疗救治才能救命,所以我呼吁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医疗救助体系。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国家安危、人民安危系于一身!”
“感谢党和国家的英明决策,感谢从全国各地来的十几支医疗队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抗疫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他们是真正的英雄!”采访最后,张旃难掩激动。
“2003年的SARS在党和政府的正确科学指挥下很快得到了控制,相信这次我们同样能够更快地控制疫情,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张旃充满信心地说。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