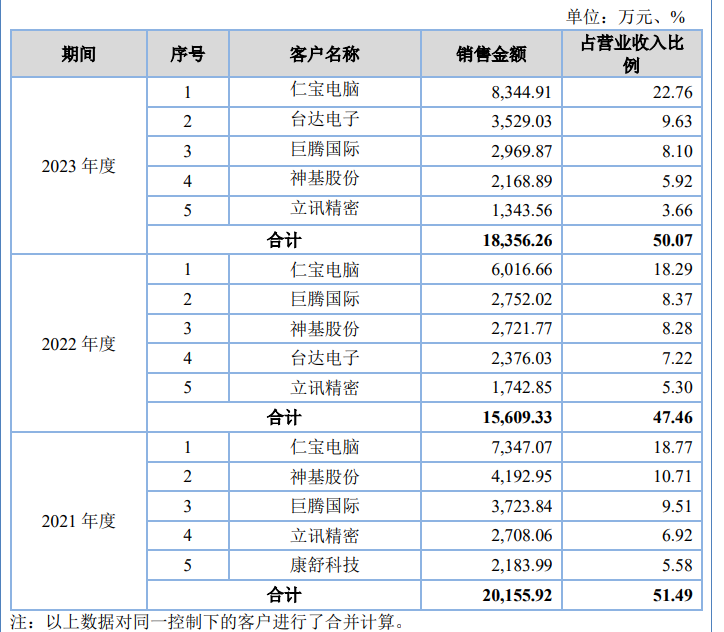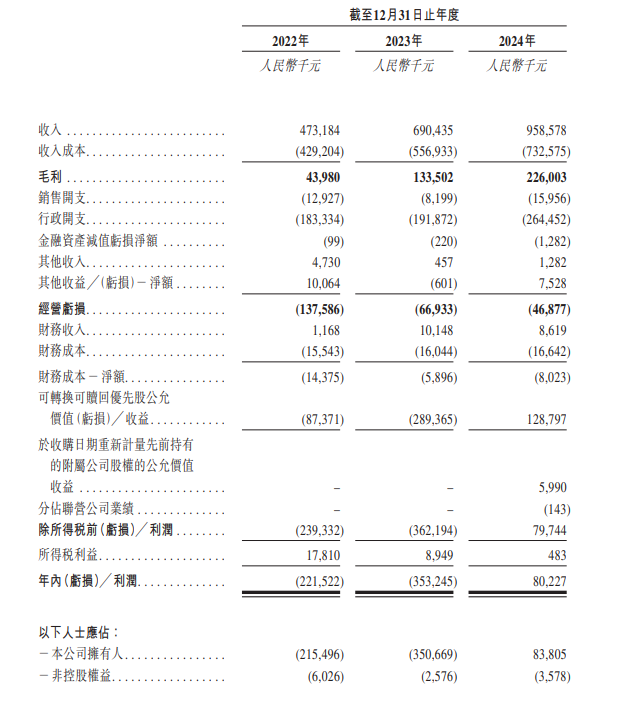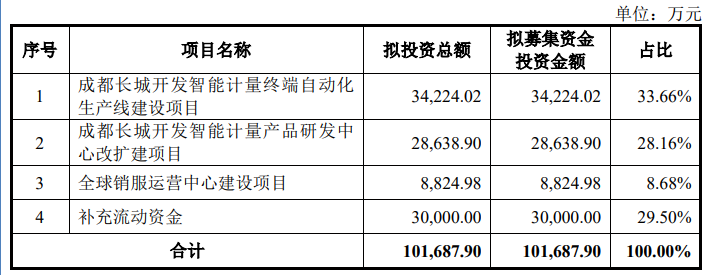封面图|《活着》
文|冯仑(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几年前出差路过嘉兴,我还去过一次王店镇。那天,我和一位当地的朋友在镇里的街道上走。镇上的主街,一边是临水的,还有一边不临水。我们沿着主街临水的那一边走出来以后,拐到后边,走到了不临水的这一侧的外墙,看到一片工地,有一个大院子正在整修,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枝丫伸展到院子的高墙之外,院子门口还立着一块文保单位门口常见的方石碑。
我很好奇,就问,「这是谁家的院子,居然还是文物?」
朋友说,「这个地方过去是胡家的。解放前,胡家应该算是我们这边的首富。」
我心想,这小镇上的首富在当年应该也有很雄厚的财力,因为这个院子看上去相当不错,像是一个缩小版的苏州园林。

于是我问朋友,「这个首富是做什么生意的?他们家后来怎么样了?」
朋友说,「胡家当年做什么生意,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家里人的故事,我听说过一些,当然都是八卦故事。」
我说,「那我也很感兴趣,你给我讲一讲。」
朋友说,「据说这个胡首富很有钱,当时,镇里的人都称呼他为胡老爷。胡老爷的院子很大,但是可能他在金钱方面命太好了,其他方面就有短缺,他的太太没有生养。于是他就跟丫鬟好上了,丫鬟偷偷给他生了个儿子。但是这样生儿子,在当地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得遮掩这个事情。
他就在家里定了个规矩,虽然丫鬟是儿子的生母,但是她不能在家里认这个儿子,她只能当保姆。儿子必须变成太太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儿子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要称太太为妈妈。
所以,在一开始,镇上的人以为这个小孩是太太生的。这个保姆也仍然是一个保姆的身份和形象。胡老爷就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他们家的体面。
但是小镇上是没有什么秘密的,很多人就开始议论。这使得这个保姆非常痛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内心有些扭曲,每天得看着自己的儿子管别人叫妈妈,却把她这个亲妈当保姆。更委屈的是,这个保姆既不敢告诉儿子真相,也不能跟儿子私下亲密说话,还得像伺候别人家的少爷一样伺候孩子,内心非常痛苦,还不得不在外面维持和谐体面的样子。」

我说,「都这样子了,他们家不吵架吗?」
朋友说,「大家猜测,他们关起门来吵过,但外面人看起来还好。」
我问,「那大家怎么知道这个丫鬟当时很痛苦呢?」
朋友说,「在 1948 年前后,胡老爷生病去世了。他死以后,这两个女人便不再和平相处,吵来吵去,镇上的人就都知道了。1949 年后,他们家的东西被充公,这一家人也就散了。紧接着,太太被斗争,这个保姆算是在旧社会受压迫,这时扬眉吐气,翻身了,变成了上等人,她才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清楚。当时她儿子都十几岁了,才认了这个亲妈。」
我开玩笑说,「她这儿子倒是没受过苦,哪个太太是上等人,他就管谁叫妈。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朋友说,「这个儿子还算争气,读书好,后来考上了大学。」

有一天吃晚饭时,我突然想起这事儿,于是跟我妈讲了朋友告诉我的这个故事。我又觉得有些余兴未了,便问我妈,「镇上当时的那些有钱人,后来的结局都怎么样?」
我妈说,「我记得当时镇上有个说湖南话的人家,很有钱,但是他们在镇上做生意的时间很短,也就三五年功夫。」
我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妈说,「有一年,镇上突然来了一对夫妇,说的是湖南话,跟我们都说的嘉兴话很不一样。王店来了两个说湖南话的,我们当然就很关注,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他们来了以后租了很大的房子,然后就在镇上做生意,好象也卖药。记忆中,他们很快就超过了镇上开店的那些小老板。」
我问爸,「您有印象吗?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我爸说,「我记得。这对夫妇很阔气,很大方,穿得也好,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到了王店不久,那个女的就死了。女的死了以后,那个男的看到镇上一个竹货店家的闺女长得挺好,就想娶她。这个人就托你奶奶做媒。于是你奶奶就帮他说合这个事。竹货店这家人,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直接就同意了,觉得这样的话生活会变好,就把女儿嫁过去了。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到了 1949 年了。全国各地都开始斗反革命、抓地主、抓阶级敌人。突然有一天从湖南来了一些人,把这个人抓回去了。」
我问,「为什么抓他?」
我爸说,「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办班参加工作,才知道原委。他们原本就是地主,在抗战结束后,就带了一些金银细软,来了浙江。发现王店这个地方不仅富裕、安全,而且能做生意,就在这住下来了。没想到 1949 年以后,他们的老家开始斗地主,发现地主早就逃亡了,于是就去找,顺着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找到了王店,就把他们带回去了。」
我又问,「带回去了之后,他是什么结局呢?」
我爸沉默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肯定是受苦了,结局不会好。」
我想,也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被枪毙已经是大幸了。至于其他的苦,能想象到他们应该都受过。

我说,「可是奶奶给人家介绍了一个姑娘,那姑娘后来跑哪了?」
我爸说,「那个男的被抓走之后,这个姑娘也就没消息了,好像跟他一起走了吧。」
我说,「你们镇上当年的那些有钱人,命运似乎都不是太好。」
这个时候,我妈看着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赞同我的感叹,但我想,她应该是认可我的这个观察的。在这样一个小镇上,当年这几个有钱人的故事都没有完美、幸福的结局,但却是那样的真实。
本文系冯叔新作《避疫六记》之四:《持箸记史》的第二篇。
过去一个多月里,冯叔和大家一样,为了躲避疫情,宅居在家。从繁忙的工作中闲下来,读书、写字、健身,和家人一起做饭、喝茶、撸猫……冯叔把这些闲暇中的点滴和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写成若干篇文章,命名为《避疫六记》。